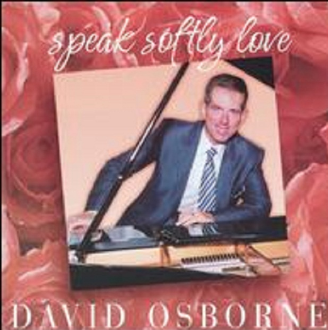如果故事有结束,应当结束于一个囚禁于高塔的精灵。
也许是一名不称职的指挥官,也许是一名混日子的士兵,这没什么差别。我的军队战败,而我成为俘虏,被迫在此处度过漫长窒息的时光。
时间过去了多久,我并不记得。它只是一种漫长。漫长到守卫或许已经遗忘了我,囚室的房门紧锁,锈迹长出锁孔。所幸精灵不需要进食,可这里阳光也同样稀少。
囚室四面砖墙,只有一道我不能企及的,狭窄的高窗。连日月的光辉也极吝啬从它只中穿过,为我降下。
然而此刻,我能感觉到外面在下雨。
潮湿,如同病毒、黑暗、嫉恨和爱,如何能阻挡或遮掩呢。
水汽从唯一的入口,从砖缝,从墙边的苔藓,向我浸润过来。它们渗透我干涸的鼻腔,进入我枯萎的肺叶。
它们携裹着天上的风,地上的泥土,空中的尘埃,进入我。
它们包含着一千万种物灵,生的与死的。
我吸入它们,一个世界在我体内拼凑。
这时,我想起我的爱人。
我的爱人啊,有着金子一样的长发和心,而他的眼眸比得过最冷烈的刀锋。我无数次地拥抱他,在鸣鸟飞尽的林木;在晨雾未散的小径;在鲜花遍撒的原野。我与他拥抱,可同时感受他柔软发尾,和坚硬骨骼。
我的爱人,正在后方的家乡等待我。
家乡已不再是家乡;而我已将他遗忘已久。我同每一个毫无心肝的军人,只知在战场上头脑空白,血液沸腾。
而今天下起了雨。雨水和囚室,冷却了我。
我思念起了你,我的爱人。
那雨滴把你的消息带给我。它们说,你在我们的土地上盖起一座高塔,一座没有门窗,只在塔尖有一扇遥远,无法触及的通风口的,封闭的建筑。
你搬去住在那里面。
雨滴说,此后便没有你的消息。树上的绸带换了一种颜色。
它又说,我来源于一个年轻人的眼泪,又被一声轻轻的叹息送进风里。
我的窗外仍旧在下雨。它的气味变得腥且咸,像刚从战场上横流的血河中打捞起来的,又被未亡人的眼泪与怨恨浸泡过。
我在战场上时常收到你的来信。里面没有蓝松鸦和霜;是微笑鸟的尾羽,哭泣木的木心。你为我寄来一支笔。
我用它蘸满我热忱的血,会自动写下你思念我的诗。
这是你的小把戏,要我尝一尝你千分之一的疼痛。而我希望那诗永不停止,我不厌其烦割开无名指的伤口,让血不住滴在笔尖上,让你留在纸上。
然而写着写着,那笔就赌气似的停下了。然后爆出一小点火星,把整支笔烧掉。
每当这时,我总忍不住要笑,像恶作剧得逞的小孩子。我听见你说,“够了,Jon,你不懂得一点节制吗?”
我是懂的,亲爱的。可你是我唯一能够毫无节制的对象。
你气急败坏的样子可爱极了。但这也意味着你将不得不再为我寄来一支笔。你又要深入迷雾重重的森林,为我找来微笑鸟的羽毛;哭泣木的木心。
而我又要像个酒色掏空的昏庸将军,头脑昏聩地去指挥第二天的战斗。
可能就是这个原因,我们才会打败仗呢?
我的爱人没有反驳我。没有像他一贯牙尖嘴利,傲慢地对我说,
“绝不,是你太愚蠢。”
窗外的雨忽然停了。
——如果故事有开端,却起源于厌恶。
对战争的厌恶,对逼迫的厌恶。宁愿放弃参战,宁愿投降和失败。
于是两个都要牺牲,一个站出来,推到前线;一个忍受孤独。之后一个迎接审判,一个迎接结束。
这场不体面的、侵略的战争,它应当破灭,埋葬于欢声笑语的未来,而这未来亦会埋葬我们。
那高塔,是你我相依偎的坟墓。
我们在那一同死去,正如在彼此身体里一同出生。
“我的爱人啊。”